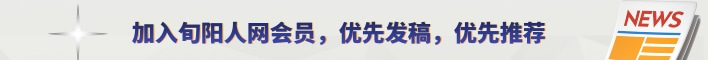一个可敬而又可憎的恩师 文/任登庚
我的启蒙老师朱先生年过古稀,身体硬朗,现已经搬到太极城城居住,和我算是邻居了。我经常在街上遇见他,每次只是很恭敬的喊一声“老师”,这算招呼了。他听到后只是驻足一会儿,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的各自瞅着脚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说,真的是人在咫尺心隔千里。然后,然后就是各自默默的离开。我也多次想过不能对老师这个样子,见面应该说上几句过去的事以表示亲近。但每次立下的决心都是在每次见面时被推翻,因为我一见到他的面时,大脑里就显出了他那害我的嘴脸,那一桩桩往事确实对人刺激的太深了,太深了……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朱老师在那里去教书的时候,我已经八岁。严格地说,我最初进学堂并不是从他手上开始的,在他去之前我就从魏老师手上启蒙,魏老师教了一年就叫我升二年级,他把书发给我以后,我不愿意,认为一年级课程好学。魏老师批评了我,我当时把书甩给他回家了。没几天魏老师被调走了,来了王老师。王老师了解到情况以后就去家访,征求大人意见以后叫我仍然上一年级。王老师教了两个星期又调走了,来了张老师。张老师教了大半学期才换来了朱老师,学校从此算是安定了。我到二年级以后才知道原来教师在一个地方是必须要呆够一学年的,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那样瞎搞? 朱老师到我们村学校时是一个人教四个年级,他教到第四年的时候学校增添了五年级,增加了一名教师。这样,我们学校就成了完全小学(1988年以前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
朱老师把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小学五年级,在我还剩下一学期就毕业时他被调到了公社七年制学校。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是两年制,七年制学校就是兼任辅导站的初中学校。 我由于自小对朱老师有些“虚”,认为他调走我们这下就可以摆脱“魔掌”了。但生活偏偏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也许是缘分注定吧,朱老师走的第二年我上初中,偏偏他又是班主任。他还是像带小学生那样,到我们村把我们几个老淘气学生一次带到了七年制学校。这样,朱老师就算一年不空地把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初中毕业。
凭良心而论,我所学的每一点知识都是朱老师辛勤培育的结果,我甚至觉得自己性格、言行都有朱老师的烙印。恩师,对我影响太深了,感触太多了,他的教育之恩我在长篇小说《变迁》里面还作过大篇的记载。 我们在上小学时,社会上对于家庭成份普遍重视。朱老师家是地主,按他自己说的就是“我出身于剥削家庭”。地主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的,但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家庭出身,重在个人表现。”咋么表现呢?就是要勇于和家庭出身划清界限,站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来。 朱老师对自己的改造可谓努力,他对于本职的教学工作简直认真到了癫狂的地步。学生作业要按时交,不合适的他上门去辅导,写错一个字必须重新再写一百遍,这是学生最害怕的事。从政治思想上也特别讲究,对班上那些老贫农家的娃子另眼看待,特别是对于军人家属的孩子那真的差点顶到头上。
我们班三娃他哥在队上当干部,加之三娃年龄比我大三岁,我们学习成绩自然不如他。朱老师就以三娃作为学生的榜样经常表扬,他对我的评语是常挂在嘴边的那几句话:“荒唐,性格孤僻,爱打人骂人。”而三娃则是“学习踏实,成绩能过得了硬”。更为可笑的是他对于军属,他看到元娃的哥在当兵,就把元娃促到了显赫的地步。元娃在学校时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所以学生们认为他在校就是错的也是对。最明显的要算选元娃当干部了,在学校,当时根据战备形势,——哦,说这些有的人可能不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都听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朱老师就把五十多个学生分成六个班,开始时叫元娃当三班的班长。元娃工作也很积极,朱老师就把三班树立成全校的红班,元娃自然就是红班长了。过了一阶段,老贫农的娃子义娃当班长的六班落后了,朱老师就把元娃调到六班去扭转形势。元娃也争气,很快就把六班搞得附和了老师的意思。这下了不得,朱老师在全校号召向元娃学习,并说他是“走到哪班哪班红的好班长”。这还不算,他还把元娃的先进事迹汇报到大队党支部,以显示自己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有功。
朱老师的汇报得到了大队支部书记的重视,于是就向公社领导推荐他当先进。当朱老师知道自己在公社领导心目中有了影响以后,就顺势向大队党支部申请,要求加入党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在轰轰烈烈的反修防修运动中,我们那可爱的朱老师把教室大门口用青石条埋嵌上了“埋葬帝修反”几个大字。 学校门前是几百人来往的大路,青石做成的那几个字露出地面一寸多高,这使得来往的人很不方便。于是,大家过一次,骂一次,搞得怨声载道。过了一年多时间,朱老师在众人的一片抱怨声中不得不把那几个字“埋葬”了。 朱老师为了入党,更为积极的表现是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去工作。他家在县城边,离我们学校八十多里路。那些年各种运动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大队干部在开会时顺带讲了几句话,内容是要求学校好好配合。这话犹如圣旨,在放暑假的时候,朱老师把几十斤重的有光纸背回家,耐着酷暑,一个人写呀,画呀,为大队办了十几份板报。办的最大一张板报是在学校对面的农家墙上,三层楼高的通两间墙壁,一直从上面房檐接茬直到下面的墙脚,那可真叫“雄伟壮丽”!我至今还记得板报两边的标语,那是我在小学时见到的最大最长且最能震撼人心的长幅:
上联是:反修防修永保无产阶级专政
下联是:深入批林批孔提高路线觉悟
那板报,大队干部看了十分欣赏,公社干部见了也夸奖。但可惜的是,尽管朱老师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拼出了全力进行表现,但他的入党申请到底没有被批准。其理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条:家庭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还要长期考验。唉,可叹,他一直到退休也没被考验成熟,一生与党组织无缘!
也许是朱老师在前途上不如意,或许他想继续表现以争得组织的信任,他在全力树立标兵的同时,对于那些出身不好和看不顺眼的学生就用尽手段打压。学校最受排挤的是军娃,由于军娃家是地主,所以朱老师每次点名批评班上的落后现象时,哪怕拐弯抹角也要把军娃挂上几句。 我们念书时学生们有的离家远,冬天到校都拿有木炭,就着老师做饭过后的火渣引着烤火。贫农家的学生经常到厨房去铲火老师还给帮忙,军娃家是地主,由于害怕老师,有一次躲着去铲了几个火炭恰好被朱老师撞见了。这就闯了祸,军娃当场受了批评还不算事,最后朱老师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把他指教的眼泪长流。末了,朱老师点着军娃的鼻子说:“我看你军娃一辈子都做不成个好事!” 在校,我家虽然是贫农,但和军娃的处境差不多。不过小有区别的是我二哥当着生产队长,朱老师在处置我时没有像对待军娃那样的露骨。 我们弟兄五个,我是老四。我大哥自小随爷爷在大岭公社柏木垭大队居住,我兄弟自小出继到双河的姨夫家,这样我就是老家弟兄三人中最小的一个。二哥和三哥比我大七八岁,我这个小的自然就站着优势,被两个哥哥宠爱,在家好吃好喝先尽着我,干活他俩扑在前。由于这些原因,朱老师经常在学生面前说我“娇生惯养,厌恶劳动”。他为了纠正我的“错误”,惯常的手段是找我谈话。那叫什么谈话呀?放学留住不让回去,有时晚自习结束一“谈”开了,不到鸡叫不放手。造孽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有一次放星期天,母亲叫我上坡去打猪草。我早上出去,回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那真叫又累又渴又饿!但是,在我刚放下装猪草的笼子时,朱老师来喊我了。母亲见老师喊,就忙催促叫我快去,我只有极不情愿地到了学校。这一去就没好事,朱老师首先叫我站着,然后说有同学反映我在校有骂人现象,叫我从灵魂深处找原因。我做了很多方面的检讨,但他都说没有从灵魂深处触动,不老实。这样纠缠来纠缠去天就黑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母亲找来,听了一会儿就问朱老师:“朱老师,今天是星期天呀,你把我们娃子弄到这里站着为啥?” 朱老师知道我母亲对我特别疼爱,他经常说我母亲这这种做法是“护短”。当下就给解释说:“你们娃在校有些思想问题,叫他来谈一下。” 母亲立即变了脸色,“在学校整天的整你还没整够,放假了娃子一天没吃饭,你要他命吧?” 说完,一把拉着我就叫走。 朱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就笑着说:“等一下,还有几句话说完就叫回去。” 母亲当即回道:“有啥你叫到学校上课的时间说,我们娃子又不是地主,为啥放假还要叫来站着?没见过,地主能叫贫农站着!” 那年头,说谁是地主就是揭短头。朱老师家里是地主,当下也没再言语,只好眼巴巴的看着,我母亲一边说,一边硬拉着我回家了。
母亲的疼爱给我埋下了祸根,朱老师从那以后几乎隔一两天就召集全校的学生在教室围住我,叫交代思想,谈灵魂深处的问题。有几次我被整哭了,哭了也不行,同学们有的推肩膀,有的用指头捣鼻子,有的羞脸,还有的往我脸上吐痰。可怜我小小的心灵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回家害怕大人知道受气,还得装硬汉子,有几次连死的念头都有了。
我至今回忆,就说老师那样做是为了教育我成人的一种方法吧,但他在我一个小小的学生前途上做手脚,那却是让人无论如何想不通的。我在小学,朱老师写鉴定的一般离不开“娇生惯养,厌恶劳动,性格孤僻,打人骂人等等”一些贬低的词语。由于每学期都有这几句,我就戏称老师的鉴定是“十六字诀”。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和我同年的奎娃每年鉴定都少不了“该生在校喜怒不现于形,阴险狡诈,道德败坏……”。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老师给作这样的评语合适不合适先放到一边,能说得出口么? 我最恼火的是从初中毕业那件事:我们初中一个班二十九个学生,当时旬阳县有三大区域,就是东区,南区,北区。我们公社属于北区,上高中都在赵湾区。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升学讲得是推荐,当时赵湾是正式中学,甘溪区开始办“五七学校”。所谓“五七学校”就是以劳动为主,面向农村培养有文化的农民。这样就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主导思想:就是学习成绩好一点具有培养潜力的学生应该推荐到赵湾中学去继续深造,那些学习成绩差一些深造价值不大的就该推荐到“五七学校”,为培养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打基础。我在班上成绩属于耍尖子一类的,应该进赵湾中学深造。上级给的名额很清楚:我们班推荐十四名到赵湾中学,十五名到甘溪区的“五七中学”,推荐的基础名额由班主任提供。 这时,那位把我从一年级教到初中毕业的朱老师在我的前途选择方面做起了他的决定作用:他在给学校提供名额时,把我推荐到了“五七学校”。他的理由很充足,说我从小不热爱劳动,学校应该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局出发,给我加强锻炼的机会,这样将来才能使我成为合格的新式农民。
当时啊,我欲哭无泪!我找人求情,想进到赵湾中学,可是小娃子说话真的是人微言轻,又有谁理我呢?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朱老师的“好心”没有起到作用,大气候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在我们开学前的十几天时间接到通知,甘溪区也办成正式中学,我们公社所有上高中的学生都到甘溪中学读书。这样,尽管我们毕业以后回到了农村,但我也算上过正式中学。这事回忆起来,是苦?是甜?反正我觉得有些戏剧性…… 我毕业以后代理教了一年书,继之当大队会计,1983年承蒙信用社主任朱传道的栽培,招聘到公社信用社当合同工。1984年基层政权改革,政社分设,我经过组织考察,代表选举,任张坪乡副乡长。可笑的是,在乡政府分管教育时,我见到了我那自小尊敬的朱老师给当时公社报的学生档案。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的鉴定原话是:“该生在校学习成绩较好,尊敬师长,热爱体育活动,爱好文艺。但该生性格孤僻,学习荒唐,爱打人骂人。在家娇生惯养,厌恶劳动,遇事爱钻牛角。不团结同学,在体育活动中经常捣乱。希望家长配合学校,促使其改正缺点,做一名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我当下翻着看时,心里一惊:这就是恩师做的事!亏得你教小学,如果再掌握大一点的权力,那你手下人结局如何?我想把那些东西撕掉,但思之再三,这毕竟是历史,况且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就原封不地归回了档案…… 我尊敬的恩师,也许就是那么的古板,那么死眼色看人。本来按关系我应该是一生敬重他的,但自从我出社会认清了他以后,对他的那些以老师之居的“忠告”可以说是听而弃之。在1994年我任十里乡乡长期间,那天在旅社遇见了他。见面三句话没说完,他就给我说:你不应该当行政领导。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行政上就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不能胜任。他当时说的倒是一片好心,但我想起他的为人,也就没有当一回事。可以说,他的人格,他的性格和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听他的话又有何益?我知道,小学期间他所重视的几个学生并不遂他所愿,一个都没成多大气候,起码没有为社会干成什么有益的事业。而他所打压的学生倒一个个都争气,奎娃当了多年的村长,并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军娃现在也是一方富翁,两个儿子大的当了老板,小的是博士。
朱老师说行政上有勾心斗角的事这不错,但是他不明白各级各单位还是党组织领导的,大多数人是正派的。拿他的观点看问题,现实社会就是一片黑暗,那实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这人一生也不是多么如意,到底没有跨进组织大门,最后从区上文教组下放到乡办小学直至退休…… 朱老师工作认真,吃苦耐劳,传授知识细心,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不愧一个辛勤的园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样的授业恩师。但是,他处事呆板,对学生刻薄,不分主次、不加区别的故意把小事扩大去伤害以至于背后陷害小学生,我一直对这位恩师的面貌没认清。我有时也想:君子不念旧时恶,我为什么一定要记老师的这些过错呢?可是,每当我想纠正自己的时候,那敬与憎之情粘在一起却是怎么也分不开。这样次数多了我就知道,我当不了君子,况且已经到了晚年,要想再装大度却是不可能了。我始终想不通,恩师在我大脑里的两面形象一直抹不去,却是何也?
2018年1月26日写于西安千户村
作者介绍: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文TAG:
随便看看:
相关推荐:
网友评论:
模板文件不存在: ./template/plugins/comment/pc/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