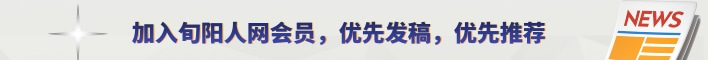豆腐往事(二篇) 文/葒菓
豆腐张
“梆——梆—豆——腐—梆——梆!”木锤敲打作为伴奏,悠长的“豆——腐”不慌不忙,从我记事起,这断断续续的“梆梆”声就代表着“豆腐张”来了。
那时候的豆腐张,已经五十多岁,可能是长期做豆腐的缘故,皮肤白白嫩嫩,头顶光滑泛着光,没有一根头发,身宽体胖,肚子鼓鼓囊囊的,从自行车上下来时,肚子还微微颤动,就像他卖的豆腐一样,颤巍巍的。

豆腐张住在我们上游的村子,和他同村的老李头也做豆腐,两个人像商量好似的,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在我们村子,要么老李,要么豆腐张。方圆几公里的村子,都吃他俩的豆腐。
奶奶想吃豆腐,一定是豆腐张来的时候。听着梆子声,哪怕远远的,也能分辨出人来。
“快出去等!你快。”奶奶给我发令了,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腿脚不便。
我领着军令,片刻不能怠慢,带着被赋予重任的责任感,几个箭步就来到了马路边,遥遥地等着豆腐张由远及近。奶奶在后面也着急忙慌地赶来了,手里端着盘子。
豆腐张心领神会地停下自行车,满面笑容地招呼着:
“大娘,今儿个几块钱?”豆腐张从来都把礼貌挂前头,不笑不说话,不喊称呼不张嘴。
“2块就够了,人少不用多了。”
“好嘞!”豆腐张揭开蒙豆腐的布,麻利地切了一块豆腐,用杆秤一摇,几乎不差斤两。装了盘,付了钱,他飞身上车,也不忘和奶奶寒暄:
“走了大娘!走了小姑娘!”他还不忘捎上我。
“慢点啊,小张!”奶奶像送个亲戚一样,目送他渐行渐远,梆子声,吆喝声逐渐微弱。
有时候,豆腐张卖完了豆腐,原路回家,看到奶奶,也停下车唠唠嗑,近乎地像亲儿子。
我曾经问过奶奶,为什么只买豆腐张的豆腐,奶奶笑了笑,说他的豆腐干净,他的头发也干净。我不禁笑出了声,大灯泡,干净又亮堂。奶奶也跟着笑。
奶奶去世那天,豆腐张碰巧遇到了,赶忙去街面上买了一提冥纸送来了,嗑了几个头。他跪下时,我第一次瞧见他的头顶,一根头发也没有。
豆腐张年龄大了,买卖让他儿子接着做,大家习惯还是叫他儿子豆腐张。
豆腐脑爷爷
我上的高中是封闭学校,只能在学校吃食堂,除了假期,没有假条是不允许出校门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和校外的商贩们里应外合,在校园的一处做起了买卖。那个地方离保安亭比较远,即便被保安看到了,学生和商贩都有时间撤退。栏杆的空隙比较宽,是几代学生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撑大的。
商贩里有一个老人被我们称作“豆腐脑爷爷”。爷爷的吆喝声别具一格:
“豆—腐—脑,还有火—烧儿!”“烧”字被他高高扬起,读成了二声,好像火烧会在他的指令下上下翩舞一般,生动有趣。
有时候,爷爷还会调皮一下,吆喝声也变了:
“豆—腐—脑—,火烧—豆腐脑,豆腐脑—火烧——”瞧瞧,爷爷的营销点子还真多。
爷爷经常是一身蓝衣服,围着一条白得乍眼的白围裙,挑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头各有一个木桶,一个木桶里装着凝脂一般嫩白的豆腐脑,另一个木桶里是浇在豆腐脑上的汁,紫菜、虾皮、木耳碎、鸡蛋花等,浓稠的卤汁鲜香无比。火烧呢,爷爷在扁担两头各装一袋子,系在桶的把手上。有白糖和红糖之分,馅料足,有嚼劲。
爷爷通常只在周六、周日下午出现,那是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吆喝几声以后,再也不需要宣传了。他在空碗里套上塑料袋,㨤两勺豆腐脑,再浇两勺卤汁。一套动作完成后,一定会加问学生够不够,不够的话再补两勺也收一样的钱。
豆腐脑加卤汁,一共2元。 火烧5角一个。
如此良心的价格,让天天吃食堂的学生趋之若鹜,尝尝鲜也未尝不可。所以,爷爷的豆腐脑和火烧,能不能买得到一定是碰运气的。卖光了,爷爷还对买不到的学生道歉,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着憨憨的微笑。
从高中第三年起,再也没遇到过豆腐脑爷爷,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豆腐脑,可那个味道永远都占据着味蕾记忆的第一名。
责任编辑:肖海娟
本文TAG:
随便看看:
相关推荐:
网友评论:
模板文件不存在: ./template/plugins/comment/pc/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