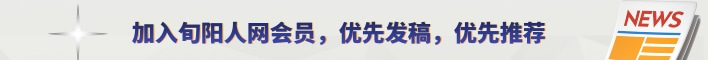康 振 文/谷去皮
康振是前年端午那天死的。
那一年康振四十九岁,在长安县的背夹旮旯啥地方租了多半间民房收破烂,一个星期顶多能弄二百来块钱,大儿子在说是名牌其实是民办的京西大学读书,星期天下午准时来取下个星期的生活费,至少得一百五十块。为了凑够这一百五十块,康振每天早上麻麻明就起来走了,一桶子开水,一块钱的三个蒸馍,一辆脚蹬的三轮车,跑遍了城里的巷巷道道,走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收书收报喽,收纸箱酒瓶喽,收旧电视机洗衣机喽!”这些话前后左右搭配着反反复复的大声喊着,中午时分坐在树底下吃馍喝凉水稍时休息,好歹收满一车子破烂蹬回来,多半把把把面、五毛钱豆腐添一洋瓷碗零半碗水,下午这一顿就吃得饱饱的了,饭一吃,嘴一抹,把车子一蹬去把货一交,少则二十来块,多则三四十块,当然也有几块、十来块的,一天弄五十块往上那是极少极少的。眼看瞎子磨刀就要快了,再有一年娃就毕业了。那天娃来了,说学校的同学们都有电脑,学动漫这专业没电脑不行,毕业班的同学有退下来的旧的,一千来元,康振没打忐忑,说你买去,我想办法,给了二百块钱娃高兴地走了。这天晚上康振加了熬煎,正巧对门老黑来了,说在劳务市场联系了个活,在六楼上把过去装修的拆掉,东西搬完,再把砖沙水泥装修材料背上去,还能拆些破烂,一共两千块,我一千一,你九百,破烂归你,干不干?康振没打忐忑,说行。两人前前后后干了十几天,把腰弦都挣断了,但算下来比收破烂还强,还能弄一千零几十块钱。娃把钱拿走后,康振长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还睡了一阵子懒觉,又蹬上车子转乡去了。几天后感觉不太谄活,腿咋沉沉的,弄啥好像没有以往劲大了。唉,出门已经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家里咋个向,喔一摊子给娃他妈一撂就走了,丢她一个人在家也够受的,回去看嘎吧。
回到家里,妻子一看:“你脸咋恁黑的,咋着哩?”“没啥事,就干了几天活。”“哎,不对,不对的厉害。”妻子眼泪唰的下来了。“甭说闲话先弄饭吃。”妻子擀了些面,炒了些白菜,把面下好捞了一老碗,油泼辣子炒蒜苗把柿子醋调得酸酸的,呼哩呼噜吃完脑门沁出了汗珠:“这一顿饭才吃谄了,我到地里看去呀。”妻趁此给在城里工作的二弟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一下,你哥不对劲”。二弟晚上就回来了,确实看到有问题:“明早进城看去”。康振靠在枕头上嘟嘟囔囔地说:“我好好的看啥哩看哩,白花闲钱哩。”第二天头明打早就坐车到商洛医院,抽血化验作B超,一查,肝癌!
康振的老家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进沟翻岭上崖后,一片稍宽稍平的沟边住了三四家人。那一年父亲病了,得的是农村人叫“细病”的食道癌,到处求医寻药不算啥,他姑父请马脚山有名的严大脚来给禳禛,弄了四两棉花,蘸上煤油放在屋梁担子上,焚香烧表后严大脚手舞脚蹈,口中念念有词,点燃棉花,屋梁上“轰”的一声,一阵黑烟火焰腾起,说是把邪气轰走了。康振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回来听说此事,埋怨母亲说我看你挏下乱子把房着了咋办呀?母亲噙着眼泪说:“好娃哩,你爸才四十八,有个一差二误,我身单力薄,手又是残残,你一个月才十七块钱,底下喔弟兄五个和梯子台台一样,咱娘俩倒咋办呀么?”熬煎归熬煎,流泪归流泪,父亲的命终究没能留得住,弥留之际看着六个哭成一团的儿子,眼睛没闭住就去了。那年康振二十三岁,老二才十六七,老三先天佝偻病瘫痪,老四老五也十来岁,老六自小被同村另一家人抱养,可怜养父也不在了,才六岁,还得管。埋葬了父亲,母亲哭着给康振说:你把书芳娶回来吧。老实本分勤快的书芳到家后,帮着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苦日子也在煎熬中一天天度过去,康振也有了自己的儿子,但谁能知道,还有更大的磨难将要降临到他头上呢!

那一年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怪处,还在四月,清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条火龙和一阵震耳欲聋的炸雷从天而降,暴雨山洪过后,康振在沟脑找着了二大(爸)和他的犍牛的尸体。二大一辈子没成家,虽然另住,但也吃喝不论,也给康振帮些忙。康振叫人给二大做了十二园的棺材,叫先生写了红绸子铭旌,埋得像模像样的。没过多久,对门那一家的男人在河南金矿出事了,丢下媳妇和三个女娃,那媳妇跪在康振面前泣声说:哥,你是好人,看在人经几辈邻居的面上,这二女子你收留下吧,康振早已泪流满面,把娃搂进怀里,哽咽中点了点头,那媳妇儿没过多长时间久改嫁走了。长期瘫在炕上的老三兄弟,原来就是肺结核,咳嗽唾痰,气喘吁吁,乃一向连住高烧不退,康振四处寻医求药,请街里有名的陈先生来给看后,又翻山越岭跑了几十里路到卫东医院买药,摸黑走到峡里,从崖上跌了下去,一瘸一跛到了家里,可怜十几岁的三弟已经咽气了,康振一扑塌坐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气来。埋葬了三弟,康振一下子蔫蔫子了,晚上窝在被子窝里默默地流眼泪。那几天,康振总是看到吃饭的时候,母亲就一个人端着碗到房背后去了,他知道母亲伤心,想一个人静静,就没在意。一次他去给母亲盛饭,无意中发现母亲在呕吐,吐出的是顽痰,带血,他好像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不管母亲怎样解释,他硬是把老人拉到了城里检查,钡餐透视一看,康振心如刀绞,老天爷为什么总是把灾难降在穷苦人身上、降在我一个人身上呢!胃癌晚期的母亲也要走了,这一刀子怎么能够割下去呢?康振卖了牛,卖了坡里的树,给母亲准备了后事。两个月后,骨廋如柴的母亲颤颤抖抖拉住康振的手,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孩子呀,------你说啥------都要把,------把这些娃带出山沟沟------,拉扯成人哪!”
母亲走后,康振彻底垮了。深夜满天密云,秋风飕飕,周围的山黑压压的一片,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唤声,把人的心揪得更紧,孤零零的几间土屋,蜷缩着一堆瘦小的身躯,康振和妻子五内俱伤,相拥而坐,泪已流干,泣不成声------,老天你真的不睁眼吗?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吗?康振心一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要用廋弱的肩膀这一座山似的担子扛起来。他辞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把正在上高中的二弟叫到跟前说:“你当兵去吧,到了部队再考,走一个算一个”,那年深秋,二弟带着红花给他哥磕了三个头走了,六七年后,成了山里走出的第一名军官。康振给四弟、五弟、六弟说:“学必须要上,还要好成绩,回到家里可以帮忙干活”。他把满沟撂荒的地都挖了,种上庄稼和中药黄芪板蓝根,天天上山挖药,割葛条,捋茶叶,扳拳芽,摘槲叶,为了那七八张嘴,只要能换点钱,他什么都干。可谁又知道,还有更沉的重担等着他挑呢!
一天康振正在地里干活,川里上来割柴的人说,你三舅捎话让你下去一下,他可能得了啥病了。康振把活一撩,十几里山路一路小跑,一边走一边拿衣服襟擦汗,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了,村口早已围了一堆人,见康振到了连忙让开路说:你舅不行了,等你着哩!康振脑子“轰”的一下,打了个趔趄,有人连忙扶着进了门,说康振来了!只见炕边围了几个上年纪的人,弥留之际的三舅已是只有出来的气,没有进来的气,知道康振来了,他说不出话却聚集了全身的气力挣扎着发出了哀求的目光,那双绝望的眼睛流出了最后一滴带血的泪,永远的闭住了!
三舅家境贫寒,四十多岁还没成起家,家里只有间半房,不知谁给介绍了一个流浪的哑巴,后来添了两个女儿,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一年,大女儿六岁,小女儿四岁,三舅去村后的坡里拔了一早上豆子,担了牛腰粗的一担黄豆回来,走到白草碥,头一昏,一跤栽得从墹上滚下来,等人们发现抬回来就不行了,就连忙叫康振。舅家的本家人商量说,这烂摊子咱谁也拾掇不起,康振是咱的外甥,叫娃下来把这娘儿仨养活了,把户口落在咱村里,不知行不行?沟里出恁多的事,死了恁多的人,到川里落户是康振最大的愿望。康振没打忐忑,跪在地上给三舅磕了三个头,然后借钱、贷款,顶着孝子盆埋葬了三舅,把山里的那一摊子一拾掇,连同妻子、三个弟弟、儿子女儿都搬了下来,在村里寻的租了三间厦子房,盘了大炕,安了大锅,这时大小吃饭的是十个人,每到吃饭时候,端碗的手围满了锅圆圈,蒸一甑篦馍一人两个就完了,每一顿都得添一桶多水。康振在山里种了七八亩地,在村里又种了四五亩地,地里的活把人干的兮兮的了,后来把山里的地种成了药还稍微松泛了些。每到麦忙的时候,康振总是麻麻明就起来,等别人到地里,他已经挖了一大片地了。中午别人还休息一会儿,他从来没有,戴一顶草帽,拿一把镰床,佝偻着腰,一把一把向前割去,就像那蚕吃桑叶一样,硬是把那一片一片的黄色的麦地吃完。到了下午,他扛起扁担,别人担两个麦捆子,他要担四个麦捆子,他知道别人扛的是一个家,而他扛的是几个家呀!地里的麦子担回来,月牙儿也挂上了山头,吃了晚饭稍微休息一下,还要给邻居帮忙变工脱粒,鸡叫了还不得睡觉。这一个麦忙下来,脸早已是黑黝黝的了,一顿能吃三个馍一老碗糊汤或者两碗捞面,走路还得抬起头来,让驼了的脊背慢慢再直起来。
孩子们一天天在长着,康振的心一天天都紧揪着。从小学到中学,家里有五六个学生,那时候学费不减免,开学的时候是最难昌的时候,康振总是先把钱给舅家的两个女儿,没打过忐忑。一天,四弟说:“哥,我不想念书了”,康振“唣”的一声:“你敢!”谁知那孩子已是铁了心,第二天给他哥留了个条子说:哥你别那么苦了,我出去打工去了,你别找我,我一定给你把钱寄回来,康振的泪珠一条线地掉在那个纸条上。三个月后,收到了他从礼泉寄回来的五十块钱,康振趴在柜盖上泪如雨下。若干年后四弟和那家的独生女结了婚,把五弟也叫去给介绍了对象成了家,他们都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成了堡子里威信很高的人,他们都知道是大哥的为人影响了自己。转眼间六弟也成了小伙子了,康振把他叫来说:“你回到你养母跟前去吧,老人可怜没有儿子才要下咱,咱不能昧了良心!娶媳妇结婚都由我来办。”六弟结婚那天,康振平生第一次喝了酒,吐了,哭了,醉得一塌糊涂。
康振心里明白,他做的这些全靠了妻子书芳,书芳和他婚结后,没买过新衣服,没抹过雪花膏,对待那些孩子们,书芳就像母亲一样去呵护他们,特别是对三舅的两个女儿,更有一片深情。康振的日子慢慢的好起来了,他从山里自己坡里剁了椽、檩,和妻子孩子们一块拉石头,拉砖,也盖起了四间一砖到顶的房子,当出嫁了那两个女子以后,他憨厚的脸上笑容渐渐的多起来了。他想,现在担子轻得多了,就丢下好好孝敬哑巴妗子,得让儿子把书念成,这两件大事完成了,我也就不操啥大心了。但谁知道,他居然病了!
从商洛医院的B超室出来,康振看了医生的眼色,心里就毛了,二弟说要去西安复查住院,他更感觉到事情不妙。尽管心如刀绞,但也装得很平静,他知道妻子他们都哄自己,说是劳累过度,他也就顺水推舟默认他们的话,他怕说破了妻子受不了,孩子们受不了!他知道他们在外边抱成一团哭,自己就把被子蒙起来流眼泪,他们进了病房,他强装欢颜,说是开水倒了弄湿了被子。在想了两个透透夜之后,他决定不在西安住院了,执意要回家:我这只是劳累了,歇歇就会好的,在这里花这闲钱干啥!
回到家里,康振叫弟弟搀着去山里老家转了一匝,挣扎着给父母的坟头添了几铣土,长跪坟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爸、妈,你交代的事情儿已经办完了------!”一月后的一个后半夜,他感觉心口一热,吐了一股子黑血,还是在天麻麻明的时候,走了!
三天后送殡前,他抚养大的那些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依然踡缩他的灵前,望着那血和泪和汗写成的挽联,悲痛至极,长跪不起-----!
挑千斤重担积劳成疾忽归去;
留百般遗憾怎不叫人泪满襟!
悲哉!痛哉!
作者简介:

谷庆敏,陕西商州人,笔名谷去皮,意在写真写实也。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发表过好多文章,总想读懂农民,读懂农村,但事与愿违。有时也夜半挑灯、奋笔疾书,但终无吸人眼球、出头成名之作。退休后闲暇无事,写些乡土文学,用百姓话说百姓的喜怒哀乐,偶尔也来几段杂文笑话,供朋友熟人茶余饭后一笑,坐得久了,也常常想起过去的艰难困苦,说些娃们听烦了的故事,心里还能有点慰藉。一生糊里糊涂,老了才弄明白,谷去了皮还真是不行!
本文TAG:
随便看看:
相关推荐:
网友评论:
模板文件不存在: ./template/plugins/comment/pc/index.htm